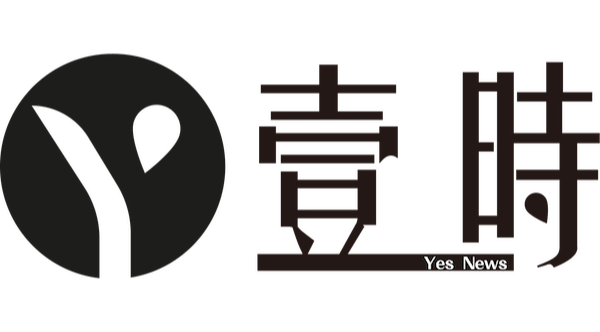文 | 李禾子
摘要:自1997年香港回歸以來,圍繞這座城市的,一方面是「世界金融中心」的光環,另一方面卻是獨立音樂日益狹窄的生存空間。與上世紀90年代自由市場經濟孕育之下流行文化的輝煌不同,如今的香港,已經越來越像一個「文化沙漠」……
「老實說我是為了兩千塊,才來到這個地方表演,玩音樂已經六年,這些年我有許多改變;譬如說我已知道這音樂不會有發展,譬如說我的旋律越寫越不自然,譬如說我已預備在某個夏天,會回到我的起點……」
My Little Airport的歌詞就像預言。2014年5月3日,維港唱片十周年紀念演出在香港最具代表性的Livehouse Hidden Agenda(HA)舉辦。當這支同樣成立十年的香港本土組合在台上唱起這首歌時,也許沒人會想到,被認為是香港獨立音樂地標的HA會在3年後險遭關停。
今年5月8日凌晨,英國樂隊This Town Needs Guns剛剛演出完畢,HA隨即遭到香港入境處人員的突襲檢查。他們聲稱演出樂隊簽證有問題,HA聘請黑工已構成違法。期間雙方發生衝突,包括場地負責人許仲和(阿和)及樂隊成員在內的7人被警方帶走。這是HA自2009年創建、且因政策轉變屢遷新址之後,遭遇的最大一次危機。
HA與香港政府的矛盾只是近年香港獨立音樂發展的一個縮影。自1997年香港回歸以來,圍繞這座城市的,一方面是「世界金融中心」的光環,另一方面卻是獨立音樂日益狹窄的生存空間。
香港是個大商場,擁擠、吵嚷、叫人慌張。與上世紀90年代自由市場經濟孕育之下流行文化的輝煌不同,如今的香港,已經越來越像一個「文化沙漠」。
Before 1997
上世紀70年代,香港工業發展逐漸進入發達期,隨之也出現了諸多社會問題。以許冠傑創作的一批粵語歌曲為代表,可以說香港獨立音樂精神開始在這一時期出現萌芽。
此前,香港樂壇一直以西方英文歌以及主要來自台灣的國語歌曲為主流,粵語歌曲則普遍被認為是下里巴人的玩意。直到70年代,香港大學畢業的許冠傑開始用廣東話創作歌曲,唱出了許多反映社會現狀、普通人生活以及諷刺時弊的歌曲。這些歌不少是他親自填詞及作曲,且題材廣泛,從描述打工仔的無奈,到描述打麻雀的心情,當中亦不乏與愛情和勵志有關的歌曲。許冠傑也因此被稱作是「香港流行音樂祖師」。
例如他在這首自己創作的《制水歌》中唱道:
又制水真正受氣,
又制水的確系無謂,
又制水今晚點沖涼,
成晚要干煎真撞鬼,
OH!真苦透呀老友,聽朝早啲起身,
搵定水桶半打,裝多啲水乜都假。
這首歌講的就是普通香港市民在70年代面臨的制水問題。當時香港不斷修建水塘,但當夏天雨季到來時,居民區一周有1-2天是必須停水的,這因而給居民的生活造成了諸多困難。此類歌曲的出現無疑也給香港平常百姓找到了一個情緒宣泄的出口。
許冠傑常常被認為是香港第一代創作並演唱社會現實的歌手。不過,雖然他的歌曲內容與我們今天所認為的獨立音樂相差不大,但鑒於時代背景,且香港樂壇仍處於起步發展階段,所以這時許冠傑的作品還不能被稱作是獨立音樂。
進入80年代,隨着香港電台、電視台逐漸激烈的競爭,以及國際唱片公司對藝人成熟的運作,香港樂壇逐步進入全面商業化時期。因而在此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里,香港歌手的演唱內容與社會、民生逐漸脫離了聯繫,大多是更易於被市場接受的情歌。直到90年代初「四大天王」的出現,香港流行樂進入了商品化的高峰。
幾乎在同一時期,一批香港的地下樂隊/音樂人也開始進入部分觀眾的視線,以Beyond、達明一派和太極樂隊為代表,他們也被認為是香港真正的第一代獨立音樂人。
恰逢80年代後期,工業中心逐漸移向大陸,香港工業發展鼎盛時期建成的工業大廈開始被空置出來,因為地處工業區的工廈與住宅區相分隔,沒有噪音管制問題,因而為這些地下樂隊提供了排練及演出空間。於是在這一時期,大量的獨立樂隊開始進駐工廈,以觀塘區為代表,巔峰時期的樂隊數量高達幾百組。他們在這裡建立自己的排練房,幾乎不受政府干涉,香港的獨立音樂在這期間可以說得到了迅速發展。
這些獨立樂隊/音樂人的作品內容貼近大眾生活,其中也有較多對於社會問題的嘲諷,因而也較少能夠在主流媒體上聽到。他們在當時香港的商業社會生存也異常艱難,有一部分類似Beyond的樂隊開始投入主流唱片公司的懷抱,還有一部分樂隊則不得不面對解散的命運。
後來,香港回歸、直至進入21世紀,MP3、流媒體以及智能手機等媒介開始出現與普及,香港新一代的獨立音樂人終於又開始以新的姿態進入觀眾視線,其中就不乏在大陸樂迷當中頗受關注的My Little Airport,由達明一派的黃耀明擔任經理人的At17,以及在YouTube走紅、曾參加《中國好聲音》的女生組合Robynn & Kandy等等。
政策尷尬
遺憾的是,互聯網並沒有給這些新興的香港獨立音樂人帶來太多他們期望中的發展。在香港,他們的生存狀態依舊難言樂觀,而當中的政策因素幾乎佔到了80%。
首先是獨立音樂的演出空間越來越小。在香港,非港籍人士進行演出,一律需申請工作簽證,否則就屬於違法聘請黑工。這一政策也成為了HA和警方的衝突點所在。曾有業內人士透露,過去幾年在香港演出順利拿到工作簽證並不是難事,但在近一年內,入境處都會詢問演出者的工作地點,凡是在HA舉行的活動,一律不準獲批工作簽證。
為什麼政府部門要斷絕HA的生意?原因歸根到底還是HA並沒能拿到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有關部門規定,HA坐落的工廈只能申請工業牌照,娛樂產業是無法拿到營業許可的。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多年來HA常常面臨著來自不同部門的阻撓和挑戰。
HA的最初選址就在觀塘區工廈。2009年,香港政府出台了「活化工廈」政策,開始准許業主申請更改或重建工廈的用途,包括商業辦公室、食肆、零售、文娛場所等等,這也在一時間導致工廈炒賣成風,租金上漲,逼走了大批生存於此的獨立樂隊;與此同時,香港政府採取的「高地價政策」(High Land Price Policy),在讓香港的房價成為世界之最的同時,也使得Livehouse等專註獨立音樂的小型演出場所生存空間變得愈發狹小。HA就曾無奈三次搬遷,還在2011年被迫停業整頓一年。
不僅沒有牌照、法律和資助等等方面的支持,政府還對公共娛樂場所提出了種種嚴苛的消防條例、噪音管理條例等等,這都使Livehouse難以在這片土地生存。
其次,政府對於獨立音樂的支持力度明顯不夠。如果說香港政府完全沒有支持本地藝術的發展,其實也並不準確。藝術發展局(藝發局)是香港政府處理本地文化藝術資助事宜的部門,以2015-2016年度為例,藝發局提供給本土藝術文化的資助達到了2000萬港幣,其中得到支持的類別包括有舞蹈、戲劇、戲曲、電影、跨媒介藝術、視覺藝術、音樂。然而,其中的「音樂」類別並不包括獨立音樂,根據近幾年的資助名單,得到支持的基本都是以古典音樂、國樂和歌劇為代表的類型。
不過作為回應,香港政府還是針對本地藝術發展,在2013年啟動了西九文化區的項目建設。西九文化區也成為了香港Clockenflap和自由野兩大本地音樂節的舉辦地。這本是好事,然而,當中的矛盾也顯而易見:面對如此大規模的音樂節,當下許多香港本土獨立音樂人尚缺乏小型現場的歷練,尚不足以應對一個大型音樂節。
與香港形成鮮明對照的反而是台灣政府對於本土獨立音樂的支持力度。以2016年為例,在台灣政府下設的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公布的補助名單中,就包括了多組獨立藝人、樂隊及公司,金額從幾十萬到幾百萬台幣不等,補助項目則包括了參與活動、展演空間、錄音室等等,例如支持本地獨立樂隊及廠牌參與SXSW音樂節。
在上周剛剛結束的第28屆金曲獎上,評審團就將年度歌曲和最佳樂團兩項大獎頒給了台灣獨立樂隊草東沒有派對,並且將首次設置的年度專輯獎頒給了台灣原住民歌手桑布伊。不論是政府層面還是社會層面,台灣對於獨立音樂的包容與理解都讓香港獨立音樂人感到歆羡不已。
音樂人的自救
2015年3月,香港第一個音樂眾籌平台,同時也是香港第一個眾籌平台「音樂蜂MusicBee」正式上線。正如其發起人、香港獨立音樂人林一峰所認為的那樣,「音樂蜂」的目標,是為更多底層的香港獨立音樂人服務。
對於很多內地樂迷來說,林一峰的名字並不陌生。從2003年自費製作專輯《林一峰的床頭歌》開始,他就一直堅持獨立發展路線。不過像林一峰一樣幸運的香港獨立音樂人並不多,《林一峰的床頭歌》最終出乎所有人預料,賣出了2萬張,這也成為他在音樂事業上的第一桶金。後來,他創作的歌曲更是被陳奕迅、黃耀明、孫燕姿等人演唱,逐漸在兩岸三地都獲得了不小的知名度。
「音樂蜂」由林一峰和他的朋友們,音樂人馮穎琪、謝國維和網頁設計師Jo & Kevin Wong共同創建。他曾在接受採訪時表示,「這個行業本來已經存在很多漏洞,不健康,現在更加艱難……錢其實是其次,這平台更重要是要聚合力量,每隻獨木舟很難持久,大家砌成一艘船,就有機會駛得遠。」對於諸多徘徊在生存線上下的香港獨立音樂人,此類平台的出現無疑是一種巨大的激勵。
上線一年多之時,音樂蜂已經有22個項目眾籌成功,共籌得資金300多萬元港幣。此外,林一峰還在「音樂蜂」發起了「Made in Hong Kong」的特色項目,用於眾籌一張林一峰和香港中樂團合作的專輯,「作為一個香港音樂人,于這個crossover中我希望做到的是:不需顛覆的創新,新派的傳統,沉澱的輕盈,謙厚的信心。」
而在去年,香港音樂人方大同也創辦了自己的個人音樂廠牌「賦音樂」。此前,方大同已經在主流唱片公司摸爬滾打多年,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根據官方介紹,「藉由着過去十多年在音樂行業中的創新與經驗,方大同希望賦音樂在秉持着最高質量的堅持之下,能體現出多元文化精神,完美地融合中國和西方的文化特色。」
「賦音樂」承擔起了培育優秀獨立音樂人的職能,借助方大同的名聲,這些新時代的獨立音樂人們自然也獲得了一條新的發展道路。
也許林一峰、方大同們的努力在如今香港這片文化的廢墟之上依然顯得微不足道,也許憑借音樂人的一己之力要抗衡巨大的政策慣性還需要一些時間,也許香港獨立音樂還需要繼續經歷長時間的陣痛,但是,他們的出現已經足以讓人欣慰。
獨立音樂在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