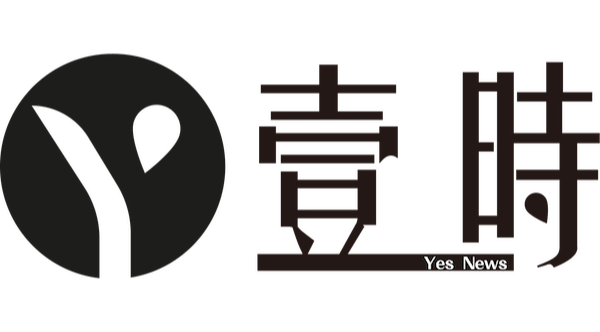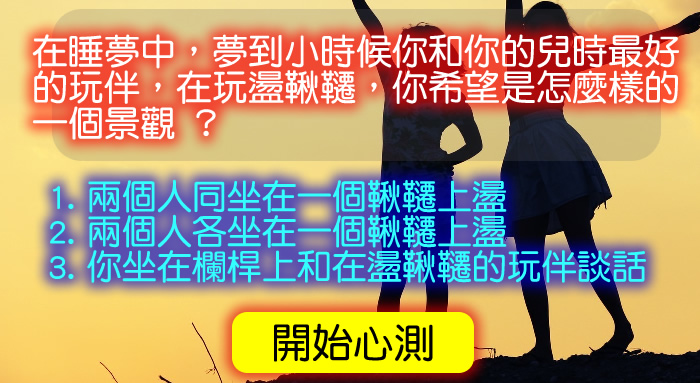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晚上七時三十分,列車穿過隧道,左邊是不知名的港灣,右邊是幾座灰濛濛的山丘。
我一定要來香港。
黑五類,打倒地主,毛主席萬歲。世界就像一個大漩渦,一切都在打轉捲進去。十多年前,我只有十歲,他們臭罵我一頓,朝我的臉吐口水,又粘又臭,然後扒光我的衣服,掛個「人民公敵」的木牌在我胸前。我門一家跪在台上,爹娘連求饒一聲也不敢,低著頭發著抖。太陽很猛,太陽每天都很猛,汗水、口水和血混在一起,蒼蠅圍著我們打轉。
列車駛到香港,列車要快點駛到香港,我差不多可以活下去!
之後我學懂了很多東西,學懂要改造思想,收藏西洋鏡是腐化。吃清蒸臚魚是剝削。杭州絲綢是人民血汗成果。我必須跟著一起喊,「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檢討身為地主女兒的錯誤。我懇切請求人民原諒。世界就像個大漩渦,一切都在打轉捲進去。爹死了,娘瘋了,爺爺不知到那裡了。
到了香港我便可以繼續活下去!我只有二十多歲。
人民有新工作給我。豬欄裡的豬很肥,牙很尖,一雙細黑眼睛盯著我,流著口水,又粘又臭,大鼻孔嗅著我,我懂得牠的心思,因為我也很餓…很餓…很餓…幸好人民還是寬容,我住在畜棚另一邊,和豬隻隔著一個破爛木欄。每天都很忙碌,餵豬,那麼牠吃飽了就不會吃我…扒豬糞,送去灶房那邊做燃料煮飯…飯不是給我吃的,我吃豬吃的餿水,我總是吃第一份。我只想活下去。
火車窗戶很髒,暗燈下約略見到一個紮著長辮的姑娘,頭髮又亂又髒,臉又黑又黃。
十多年過去,人民很寬容,寬容得忘記了我的過錯,他們忙著勞動生產的事,忘了我是「人民敵人」。幸好我的家人全都死去,沒有人會重提我的背景,叫我的名字,人民只記得我是養在豬欄的餿水妹。終於,我再不是萬惡地主的女兒,可以穿衣服,可以著鞋,可以吃米糠。我終於活了過來,那些又肥又臭的豬沒有吃掉我。
上天佛祖觀音菩薩,保佑我,保佑我進得了香港。
世界就像一個大漩渦,一切都在打轉捲進去。今年初,人民再次搭起了大台,一條「打倒階級敵人,毛主席萬歲」的大紅橫幅下,黑五類跪著,太陽同樣很猛,蒼蠅在舔他們身上的口水、汗水和血。最後人民打得黑五類皮開肉綻,綁起來活生生扔進河裡去餵魚。
火車跑得太慢,可不可以快點?
聽說領導逐家逐戶找一個叫「伍賽珠」的女人,今年應該二十多歲,是地主伍氏的小女兒,組織那邊沒有她的死亡紀錄。天呀!根本沒有「伍賽珠」這個人,我是餿水妹呀。對,要冷靜,要活下去,我不能給拿去餵魚,爺爺說過有個叫香港的地方,他在那邊做生意,樓很高,錢很多,他們餐餐吃乳豬燒鵝,喝頂級普洱。這個地方在火車線的盡頭,那邊沒有人民和領導。
火車站大門掛著時刻表,「四月七日早上五時半 香港」。
我終於走運了嗎?沒有人守著月台,我立刻潛進客車廂,似乎全鎮都到大台那邊,他們剛剛打倒了組織領導,興高采烈,沒空管檢查車票這種小事。火車發動,轟隆轟隆,簸箕著向前走,向香港走,經過三塊水稻田,一片叢林,兩座城市,忽然停了下來,有幾個軍人上車,說要查證件…完了…完了…沒救了…但軍人只掃視一眼車廂,不知為何,眼神好像有點哀傷,他們略略查了幾個人,便掉頭下車,真好運,也許他們都忙著鬥垮階級敵人,沒空閒逐個檢查。
火車再次發動,過了半小時,天差不多全黑,左邊是不知名的港灣,右邊是幾座灰濛濛的山丘。我受了那麼多苦,總算走好運了,我會活下去的…快點到香港吧…「驗票員查票!」前方有幾個穿制服的在查票,一行一行,逐個逐個,一絲不苟地檢查,這次可逃不過去,要回豬欄吃餿水,要跪著給吐口水,要做魚糧了!不,我可不能給抓回去,明明一切是那麼順利,只要不給抓住就行。我打開窗,火車原來跑得很快,風很強,但我運勢正強,沒問題,閉眼跳下去,不會粉身碎骨的,只會擦損一點吧。
卡喇!
辮子卡在窗框縫裡,連著皮血淋淋吊著,火車飛馳而去,身體掉到草地上,翻了幾翻,頭顱歪歪斜斜地倒在肩上,斷了,我痛得失去知覺。
世界就像一個大漩渦,一切都在打轉捲進去。我終於來到香港了嗎?不管如何,在我抵達香港之前,我都會活下去,一直沿火車線走下去,找個途人問問吧…時間好像過了很久,我走了好多好多的路,一路都是晦暗不清,沿途只有幾個略可辨認的人影。
「我終於來到香港了嗎?為甚麼不回答我?為甚麼要害怕?」不要緊,我會一直走下去,直至走到香港。